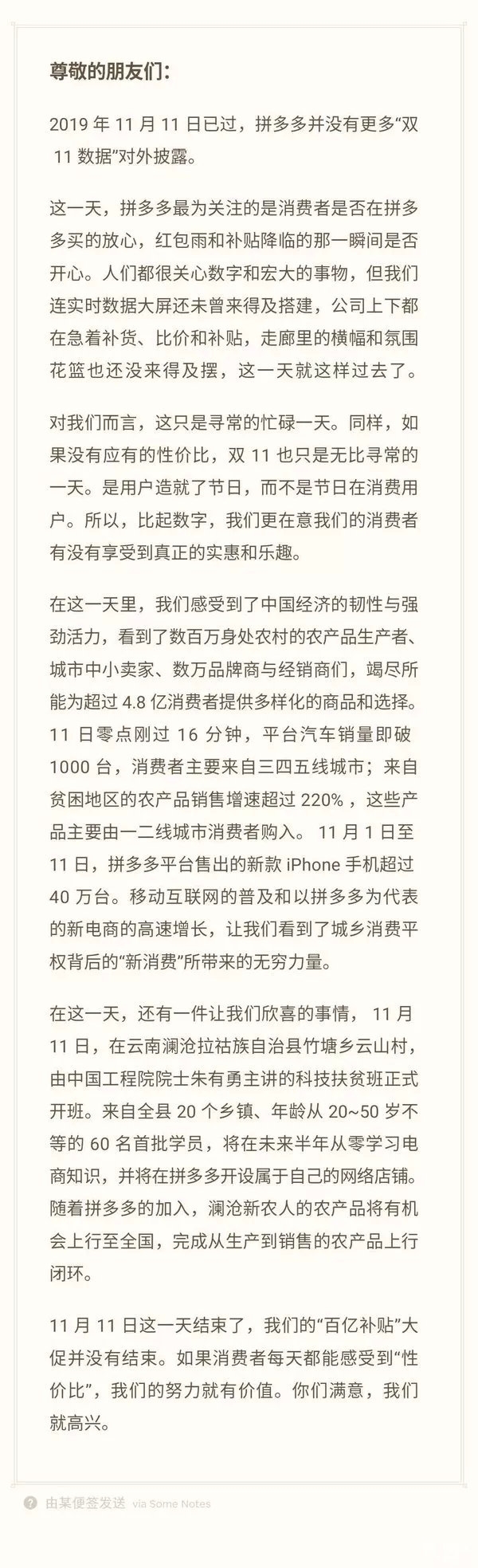引言
唐伯虎何许人?有人会说,他是江南四大才子之首;有人会说,他文武双全,智斗宁王;有人会说,他风流倜傥,为爱点秋香。
但问题是,这些是唐伯虎,还是我们印象中的唐伯虎?这些或许是唐伯虎的片面和美化后的他,但绝对不是真实的他。
 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真正的唐伯虎,其实是个一生不得志的寂寥落寞人。
他内心深处的无奈,和王维有些类似,最后都皈依佛门以寻求心灵的慰藉。
王维说:
“一生几许伤心事,不向空门何处消。”
而唐伯虎则说:
“满腔清思无人定,付与诗篇细剪裁”。
其实,在唐伯虎的诗歌思想内涵中,就有不少佛家的思想融入其中,或者至少可以说是与佛家的部分思想是相通的。
只不过,其实对于唐伯虎而言,佛教里的一些思想,诸如自由自在,诸如修来世,诸如活在当下这些,最有用的便是能帮助他避世,给与他精神上的慰藉,仅此而已。
唐伯虎的作品中体现佛家思想内涵,其内核是为了逃避现实
首先,唐伯虎晚年自号“六如”,这个便是借佛家思想来进行逃避现实世界的一个典型代表。所谓六如,便是取自《金刚经》中的那段
“一切有为法,如梦幻泡影,如雾亦如电,应作如是观。”
单单从这个自号我们便可以看出唐伯虎内心的期望,期望这个世界的一切,都和金刚经里说的一样,一切都是镜中花水中月,一切都只是一场虚空的幻境。
自己可远离,甚至逃离这个令他十分不舒服的虚幻世界。
在佛家的思想中,人生就是修行,红尘俗世的一切都是虚妄,是迷途和苦海。只有皈依佛家,内心深处才能拥有真正的快乐,才是真正拥有无上智慧之人的选择。
而唐伯虎在自己的诸多诗词之中,都表达自己对这种思想的支持和推崇。
唐伯虎有首《爱菜词》,里面有“颜子居陋巷,孔子厄陈蔡;饮水与绝粮,无菜也自耐”的句子,更直接写到
“我爱菜,人爱肉;肉多不入贤人腹。厨中有碗黄齑粥,三生自有清闲福。”
对于这首诗的解读一般都是说唐伯虎以古代先贤自比,要向颜回合孔子一样,对于饮食方面不要有太多的执著。
表达唐伯虎率真简洁,雅量非常的高士之风。但这首诗词中,其实便有唐伯虎思想中的佛家思想内涵的核心,借佛家思想来逃避现实。
爱吃菜,不爱吃肉。典型的素食主义推崇,倒是和佛家戒荤腥符合。但更多的不过是唐伯虎掩饰自己的窘迫,寻求精神上的自我安慰而已。
唐伯虎青少年时,富商家庭出身,衣食无忧,又少年成名。那是意气风发,自命风流,会同三五好友,是那秦楼楚馆之常客。
别说吃素吃菜了,饭菜里的油水少了半点,他都受不了。那时的他,怎么可能是爱吃菜的人。
但天有不测风云,他自科考舞弊案后,不但终身失去了科考的机会后,在那之前家中商业事物也是连遭打击,父母妻儿还有出嫁的妹妹都前后离世。
生活陷入了绝对的困境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,他唐伯虎写诗,说自己爱吃菜,不爱吃肉。肉食者鄙,吃肉的人都是庸俗之人,我这种有佛性的“高人”就会选择吃素。
这完完全全就是在逃避现实!
现实就是他唐伯虎晚年家境贫苦,想要吃些好的,他也吃不了。
于是便接着佛家的思想,来说什么爱吃菜好,以此来给自己“洗脑”,让自己忘记自己在生活中的困顿,好像自己真是因为喜欢吃菜,才不去买肉吃似的。
还有他在《警示》中写什么
“万事由天莫苦求,子孙绵远福悠悠。饮三杯酒休胡乱,得一帆风便可收。生事事生何日了,害人人害几时休。冤家宜解不宜结,各自回头看后头。”
这首诗词之中,颇有一番命运由天来定,一切都是上天安排好的。如同佛家思想中的
“预知前世因,今生受者是。预知来世果,今生做者是。”
颇为吻合。认为今生今世的一切,都是因为自己前世的行为所决定的,自己也好,世人也好,不论如何努力,都无法有任何的改变。
这是他唐伯虎在面对自己仕途无望,人生找不到努力的方向后,通过佛家修来世的思想来安慰自己,来逃避现实。
劝告自己之所以会因为舞弊案失去当官的机会,都是命中注定的事,是无法改变的事。劝自己不要继续去执着其中,要学会放下,不必介怀。
个人以为,若是一切都是上天安排好的,那世界上的人为何要努力改变命运!只有那些认命了,认输了的人,才会这么认为。
而无疑,被现实打压到了没有翻身之机的唐伯虎,选择了认输,同时,也通过佛家的修行来为自己的放弃自我开脱。
为此,他甚至在《绝笔诗》中写出了
“生在阳间有散场,死归地府也无妨。”
这话怎么看都是他对于自己的一生并没有什么留念的,人间也好,还是佛家中的地府也好,对于他没有什么区别。
可见对于逃避现实世界,逃避红尘,他唐伯虎是有多么的向往。
而佛家的思想内涵,也正是当时他最为需要的思想。所以在他的诗词中,都可以看到佛家避世思想的体现。
“不争不抢”的淡漠名利心态,也是用佛家思维来麻痹自己
佛家的思想里面,清净无为,不与人争,是备受推崇的内容。认为去争名夺利,都是庸俗之人才会去做的事。
遁入空门之人,就应该超然物外,淡薄名利,不去图这些“虚无”之物。在唐伯虎的诗词之中,这种思想也多有体现。
他的《睡起》中写
“世人多被鸡催起,自不由身为利名”
说的就是在他眼中,世界上大多数的人,都在鸡鸣之时便已起床,开始一天的辛苦劳作,经商的准备货物,上街叫卖,当官的开始准备官服,收拾心情去和其他同僚虚与委蛇。
唐伯虎也算是看得透彻,觉得大多数人都不会因为早起去忙碌事业而开心快乐,但是这些人又不得不早期奔波,或许是为了那几两散碎银子,或许是为了自己能升官发财。
但不论如何,这些行为,都是被利益所驱使,丧失了自己的本性。在唐伯虎看来,是很不值得的。
唐伯虎由于自己根本没有去追逐名利的需求,也没有追逐权利的资格,所以他放下了,身上没有这种压迫感对世上的许多事,也就看的越发的透彻了。
他仿佛达到了佛学思想中超然物外的格局,从旁观者的角度,以一份淡漠清闲的心态来看世间忙碌之人。
一方面体现了他的淡漠名利,另外一方面,不也是佛家思想中的清净,不争的思想优越感的体现吗?
在唐伯虎的《叹世》一诗中,也表达了相同的思想意思。诗中写道
“一寸光阴不暂抛,徒为百计苦虚劳。观生如客岂能久,信死有期安可逃。”
意思就是人们把时间都浪费到了各种算计和谋划上,把最有意义的时间,白白浪费掉了,没有用在享受人生上,而是终日劳碌,却不知道生命有尽头。
到了生命的终点处,没有人可以躲避开,但是不同的人,其渡过生命的方式是不同的。有的人一生充实,有的人一生庸碌无为。
而在唐伯虎看来,终日为了利益算计的人,便是那种人生没有意义的人。
而这,也和佛家与世无争,不要去被俗世的功名利禄所迷惑,而迷失自我的思想所一致。
说起来,佛教在明代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,那便是洪武皇帝朱元璋曾经当过和尚。
虽然对于朱元璋而言,当和尚不过是自己混迹江湖,混口饭吃的应急之举。但朱元璋认这个事,明代的佛教之人就会就此大作文章。
佛学思想里面,人生就是修行,红尘俗世是“苦”的,只有皈依佛门才能得到“大智慧”,才能得到精神上的“大欢乐”。
这种思想对于明代诸多不得志的文人而言,都是十分具有诱惑性的。
站在他们的角度来看,佛家的理论说得太对了,人生坎坷,科举艰难,世界上的一切不过都是争名夺利,最后不过一场空。
在这些“失败者”眼中,不论现在状况如何,是科举不第,还是当上大官,风光一世,最终的结果,都是一捧黄土。
在佛家的学说这里,他们找到了精神上的“公平”,甚至自己可以从俗世中的输家,变成精神世界的赢家,依靠佛家的理论来修来世,精神安慰自己,自己比从前那些高自己一等人,要更加的高级。
唐伯虎其实便是明代文人中的“失败者”代表,其实并非是唐伯虎有多么的认可佛家这种不去争名夺利的的思想,而是争名夺利失败的他。
只能通过佛家淡泊名利的思想,让他的精神世界找到了自我安慰的可能,找到让自己灵魂得到慰藉的场所。
若是其他的宗教思想能让他放下过去的执念,放下自己内心的不甘,他一样会为那个宗教的思想摇旗呐喊。
“地水火风成假合,合色声香味触法。世人痴呆认做我,惹起尘劳如海阔。念嗔痴作杀盗淫,因缘妄想入无明。”
唐伯虎的《醉时歌》仿佛就写出了他的心声,诸多佛家用语,如“嗔痴”,如“嗔痴”,甚至“色声香味触法”等用语都在这首诗中出现,而这首诗却名《醉时歌》,却是犯戒了的。
但是对于唐伯虎而言,佛家的思想,本来就不是全部接受,他接受的是佛家思想里面对于功名利禄的超然和不屑,对于佛家思想中的自律和其他各种清规戒律,他也是根本不当一回事的。
知足常乐的的佛家思想,是对自己生活窘迫的自我安慰
在他的《警世诗》中,有几句诗是这么写的:
“措身物外谢时名,著眼闲中看世情。人算不如天算巧,机心争似道心平。过来昨日疑前世,睡起今朝觉再生,说与明人应晓得,与愚人说也分明。”
这诗句看起来也是在强调不要一心想着争名夺利,只有愚昧短视的人,才会去蝇营狗苟,投机取巧地苦心钻营。
其实,这诗更多的侧重点在于唐伯虎自己的内心世界。在他看来,只有自己的内心平静,如佛家子弟一样有一颗平和的心,才能真正的享受人生。
但这些,换个角度来说,也都是唐伯虎主观意识上认定了人生艰难,红尘俗世中没有值得留恋的东西,所有的东西都是虚幻,都是没有价值,没有意义的东西。
所以在他的诗词之中,一心劝说读者放平心态,不要去争,要把握当下。去享受自己现在能过的生活,把自己的生活给经营好。
换句话说,还是唐伯虎自己在逃避世俗,那个他已经失败了的世俗。所以以他这个“失败者”的角度来看,这个世界确实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。
呼吁大家不要去追求红尘俗世中,那种物欲横流的享受,而是要去追求精神上的丰富。
但问题是,春风得意马蹄疾,一日看尽长安花的体验,他唐伯虎体会过吗?
那个指点江山,挥斥方遒的豪情,他唐伯虎体验过吗?
还有那金銮殿上,一策决天下之大势的那种才华得展的满足感,他唐伯虎体会过吗?
答案是他都没有体验过,他只能顺着佛家劝世的口吻,劝说世上和他一样的失意之人。
不要去在意那些他们一生都体验不到的东西,不要去为了那些得不到的东西烦恼,要把眼光看向自己能把握到的东西,经营好自己目前的生活,才是最为重要的。这也是他唯一能做的事了。
所以他写《桃花庵歌》,写什么
“若将富贵比贫者,一在平地一在天,若将贫贱比车马,他得驱驰我得闲。别人笑我忒疯癫,我笑他人看不穿;不见五陵豪杰墓,无花无酒锄作田。”
这诗词根本就不是什么安贫乐道,视富贵功名为无物。
这不过是他化用佛家的避世思想,来彰显自己自由自在,不为红尘俗世操劳的优越感,来表达唐伯虎对于不给自己当官机会的朝廷的不屑,是他的一种诡辩,甚至可以说是自我欺骗,自我安慰。
当然,也是一场精神上的自我救赎。
结语
唐伯虎的悲哀人生,由此看来《明朝那些事》中有句话说得很好:看到后世改编的影视作品中,唐伯虎有多么的洒脱逍遥,现实历史中的唐伯虎就有多么的凄凉不堪。
而在这份不堪中,在唐伯虎的诗词中,仿佛藏匿到了他对平静内心的向往这个看似“高端”的佛家思想中。
青灯古佛,枯燥平淡,内心寂寥,郁郁寡欢。一生不得志,不畅快,他却只能在佛家的思想里,找寻自己人生的意义。在我看来,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悲惨和无奈。
明明是自己没有机会去成就事业,成了一代“豪杰”,却只能用自由自在,无拘无束,不去红尘自寻烦恼这种思维来彰显自己的优越感。
而这种佛家思想,很好的满足了唐伯虎的“阿Q精神胜利法”的需求,于是被他所接纳,所推崇,甚至皈依佛门以求精神安慰。
由此看来,诗词中融入所谓的佛家思想,不过是唐伯虎最为无奈地选择,那一声声佛号中,那一首首诗词里,满满地,都是他唐伯虎的不甘,后悔和痛苦。
“我也不登天子船,我也不上长安眠。”
“闲来写就青山卖,不使人间造孽钱。”
参考资料:
《唐寅佛教诗歌思想内涵》
《唐寅诗集》
《金刚经》
《明史》